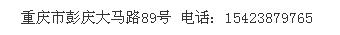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年10月出生,福建厦门人,抗击“非典”特等功臣,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的重要推动者。年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钟南山被授予“共和国勋章”。他投身呼吸系统疾病的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60余年,重点开展哮喘、慢阻肺疾病、呼吸衰竭和呼吸系统常见疾病的规范化诊疗,以及疑难病、少见病和呼吸危重症监护与救治等方面的研究,他带领团队进行呼吸疾病临床科研攻关的过程中也注重中西医结合。
与中医结缘
访谈人:在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您与他人合写的论文《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科技成果奖。您是怎样与中医结缘进行慢性气管炎的研究呢?
钟南山:这要从一个“痰”字说起。20世纪70年代初,针对我国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病情况,周恩来总理向医学界发出号召,要求广大医务工作者做好慢性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的群防群治工作。年,医院(现改名为广州医院)响应号召成立了慢支炎防治小组,医院决定抽调我加入这个小组。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自己是个党员,就应如同当初填写毕业分配志愿书一样,听从党的安排”。于是由3人组成的慢支炎防治小组就这么成立了。
然而,防治小组成立之初,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与具体的任务,就是为了响应周总理的“群防群治”号召而建立起来的,医院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是个空白。一开始,我们所干的活就是为慢支炎患者检查身体,照看患者们在墙角晒太阳。为此,我当时也有些苦恼。
有一天,我正心绪不宁地在晒着太阳的慢支炎患者中踱步,走着走着,我就瞧见了患者吐在地上的痰。在那天的我看来,它们却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色彩。看着看着,我就蹲了下去,发现慢支炎患者们吐出的痰各有各的不同,即使是一个人吐出的痰,也有不同。当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自己就要走上研究呼吸系统疾病的“正道”,预感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
不过当时我还是决定继续观察几天,掌握一些患者咳痰的规律。于是在碰头会上,我向两位前辈报告了自己的观察及所做的预测。于是小组决定,从痰样分析开始,正式制订研究方案和实验计划,真正开展起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与研究工作。就这样,防治小组找到了呼吸系统疾病防治和研究的突破口,迈出了第一步。
我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学习时做过一些生化实验,对患者咯出来的痰液进行了生物化学分解,经过实验我发现同样是慢支炎,患者的分泌物却有不同的成分。当时就考虑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治疗方法。那时,我们还跟中医科有联络,在学习中医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医对呼吸系统疾病治疗的方法:一个是对虚实寒热的分析,另一个是对脏腑的分析。慢性支气管炎涉及3个脏器:肺、脾、肾。进一步说,就是肺虚、脾虚、肾虚导致的慢性支气管炎有不同的表现,是不同的类型,所以应该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当时,我就采用了中医的治疗方法,并和西医的局部性状治疗结合起来进行,在认真向小组里的老医生侯恕学习和请教后,在侯恕医生研究的基础上,采用一种叫紫花杜鹃的草药来配合进行中西医治疗,有效率达到50%以上,效果显著。
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代表团来中国参观,到广州以后,就开始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最后来到了我所在的慢支炎小组。因为小组当时已经在慢支炎中西医结合防治、分型等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代表团专门参观并听取了我们的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年,第一届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广东省代表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盛会。当时我与侯恕医生合写的《中西医结合分型诊断和治疗慢性气管炎》的论文,被评为国家科委全国科学大会成果一等奖。后来,我们将研究和治疗领域从慢性支气管炎扩展到了对肺气肿、呼吸衰竭、肺心病的治疗,年,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正式成立。要说真正在专业领域与中医结缘,应该就是从慢性支气管炎的中西医结合诊疗开始的。
访谈人:您从年就开始将中医投入临床研究中,可以看出您对中医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这是一种怎样的感情?
钟南山:要说对中医的感情,我先分享一个小故事。年我考取了公费出国留学资格,赴英国爱医院进修。年1月6日,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前往爱丁堡大学报到。当时我的导师是弗兰里教授,他第一句话就问:“你想来干什么?”我还记得当时非常恭谨地向他说明,是想来搞呼吸系统方面的研究。弗兰里教授当时回答说:“你先看看实验室,参加查房,1个月后再考虑该做些什么吧!”第一次会见就这样短暂结束了,总共不到10分钟。
我当时走出教授办公室,内心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难道中国人真像那些外国学者想的那样,闭关自守无知吗?不!我们祖辈曾有过光辉的成绩!两千年以前,中国人就懂得使用麻黄治疗哮喘,西方的麻黄素是20世纪40年代从我国麻黄中提取出来的。中国早在明朝李时珍时,就已运用过洋金花、曼陀罗,这些都是阿托品类药,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挺直腰板站起来,用行动去为中国医生争口气。
1个月后,我在教室再次遇到弗兰里教授,正当我向他问好时,他问我:“你能不能讲一讲中国的医疗?”我当即答应下来,并精心准备了幻灯片,决心好好地把“中国医疗”呈现给大家。
我记得那天台下人很多,我从中国的传统医学讲起,讲中西医在呼吸医学诊断方法上的相通之处,讲中医是通过观察患者的舌象诊病的,比如当肺源性心脏病患者处于急性发作期,在没有对患者做动脉血气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借用中医的诊疗方法,观察患者舌头的颜色,以此判断患者缺氧和酸碱平衡的情况。此外,我还讲解了针刺麻醉,在中国长期被运用于临床治疗。在这次演讲中,我在呼吸疾病研究所所做的研究全部派上了用场。讲座结束,全场掌声雷动,我在医院学生面前的第一次亮相顺利收官。
我之所以讲中医舌象,是因为关于一个病例的讨论:一个患肺源性心脏病的英国患者吃了几天利尿药以后,浮肿的情况消退了,但是表现得十分亢奋。我当时看了一下患者的舌苔,是绛红色的,就是说属于中医常说的“阴虚火旺”。在呼吸疾病研究所工作时,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患者,他们可能因为使用了过多的碱性利尿剂,出现酸碱平衡失调,舌苔才呈绛红色。于是我对负责这个患者的英国教授说:“这个患者一定是有低钾血症,要补钾。因为患者用利尿剂太多以后,钾流失严重,所以出现代谢性碱中毒。”
当时英国同事觉得很奇怪:中国医生怎么会这么认为呢?但那位英国教授还是给患者测了动脉血气和血钾。结果一测,血气显示有碱中毒,血钾果然很低。患者补了钾以后,过了两天,情况就改善了。
当时我对这个患者的诊断,让这位英国教授对中国的医术产生了兴趣。他没想到,一个舌象会帮上这么大的忙。在后来对患者的治疗中,我还采用了让英国医生更感神奇的中医现代疗法:针刺麻醉。针刺麻醉是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所取得的一项新成就,它用于胸腔手术镇痛有困难,但是用于甲状腺手术的麻醉是可行的。“观舌色”诊疗方法和针刺麻醉技术在临床取得了实证,获得了教授和同行们的认可。
回想起来,我认为我当时的自信,不仅源于对自己祖国的热爱和血浓于水的感情,更源自对祖国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和骄傲,所以我才有了强大的底气,以实际行动赋予了中国学者应有的尊严和地位,赢得了对方发自内心的尊重。
用循证方法推进中西医结合
访谈人:您多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全社会呼吁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站地址 http://www.soegm.com//kcyfl/16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