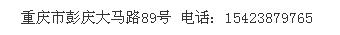
田嘉怡导读
苏珊·桑塔格
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年当选为美国文学艺术学院院士。她是当前美国声名卓著的“新知识分子”,和西蒙?彼伏娃、汉娜?阿伦特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
对于桑格塔而言,脱离她的作品来谈论她本人是不现实的的。事实上,正是她的一系列文艺批评作品构成了其进攻的刀剑与火药,正如她本人言:“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上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年《关于“坎普”的札记》的发表使她名声鹊起,年的《反对阐释》、《一种文化与新感受力》开风气之先,年的《论摄影》和年的《疾病的隐喻》更是奠定了她作为文化批评家的牢固地位。
在这些作品中,桑塔格向陈腐的美学观猛烈开火,把剖析的笔触伸到了当代社会文化的诸多症结之处,言他人所未言,扫荡了沉淀在人们意识中的许多沉疴。当作家们的生活变得逐渐制度化、工作化,成为或许被“资本社会”收编的人物们时,一个作家的勇气在于尊重复杂的真实世界。面对充满谎言、恐慌与胆怯的时代,桑格塔这位斗士,在六十年代,做出了生涯中的重大决定:“我一生的巨大的巨大改变,一个发生在我移居纽约时的改变,是我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我将在大学世界的令人神往的、砖石建筑包围的那种安稳生活之外另起炉灶”,她决心从象牙塔中走出来,树起思考与表达的大旗。
三六九十二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具体分析书中内容,可以将桑格塔所要表达的内容按逻辑划分为四个部分。
一、疾病隐喻了什么
虽然两者都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热情病,但是两者仍有不同。结核病的发烧是身体内部热量、热情燃烧的标志,然而癌症被认为是缺乏热情的人患的病。在描述结核病患者时人们更加倾向于使用“文雅、精致、敏感、浪漫、柔美、有趣、有教养、优越、悲伤、艺术家的病、妙笔生花的人的病、外显的风度、有个性……”等等词汇,而轮到描述癌症患者则基本是负面的词汇:“压抑、忧伤、焦虑、愤怒、用脑过度、冷酷、无情、被入侵、富裕、奢华、懒惰……”。在这些社会化的被普遍承认的标签下,社会、文化所赋予疾病的隐喻已经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在提起艾滋病时,这种标签隐喻带来的社会态度则更加明显。由于艾滋病的更为人周知的传播方式为性关系途径,故而在“文明社会”里,性行为本就属于人们倾向于避之不谈的领域,其隐秘性又与不洁的行为联系起来,为患病者提供了犯罪感,也为其他人提供了道德批判的依据。
其实再细分疾病,即使是在人们都不希望进入的疾病王国,被隐喻的疾病也被分为三六九等。与肺部之上器官联系紧密的使患者气息微弱的疾病,被认为是精神性的美好的疾病、贵族式的疾病,而患者的死亡也被认为是美好的悲剧,富于罗曼蒂克的气质。然而于各种器官都可以增长(更不要说某些“不洁”的性器官)的不动声色臃肿地繁殖的疾病,则被认为是邪恶的、不良的。人们在文化上已经对于身体部位做出了道德评判,又以这种约定俗成的道德评判规劝新进入文化者的行为。
二、形成隐喻的原因
在此部分作者试图给出解释,基本上可以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角度来谈。
就政治而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阶级崛起壮大,贵族退缩至历史舞台角落。与资产阶级相比,贵族此时只剩下头衔、徽章等一系列荣誉性的表征,而事实上经济命脉已经脱离他们的掌控。为了与他们所鄙视的“新贵”们区别开来,贵族们有意识地营造一种专属疾病,并通过文学加之以浪漫的风格与想象,营造一种向往。同样的,后来的略显低俗的“富贵病”则是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划分界限的战争。
就经济而言,作者认为癌症所拥有的那种自我无限增殖、膨胀式的增长、最终导致的死亡带来的人们对于癌症的不良观感反映出人们对于工业社会里经济增速缓慢但庞大的体量的恐惧——“我们关于癌症的看法,以及我们加诸癌症之上的那些隐喻,不过反映了我们这种文化的巨大缺陷: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对真正的‘增长问题’的鲁莽、草率的反应,反映了我们在构造一个适当节制消费的发达工业社会时的无力,也反映了我们对历史进程与日俱增的暴力倾向的并非无根无据的恐惧”。
此前的暴力的经济危机带来的阴影还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按照马的看法,资本主义经济会经过蓬勃、登顶、崩溃、回暖的循环,而巨大的金融怪兽在慢慢发育之后大厦忽倾带来的灾难会毁灭许多人的生活,尽管它本身会自我修复。人们生活于对未来的不确定恐惧中,则对缓慢生长的危机报以极大的恶意,甚至延伸至无辜患者身上。
至于军事方面,疾病的隐喻更像是长期默许思维在这个时代的新形象而已——“在对疾病的想象与异邦的想象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它或许就隐藏在有关邪恶的概念之中,即不合时宜地把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污染者总是邪恶的。这句话反过来说也不错:被判定为邪恶的人总是被视为或至少可能被视为污染源。类似于读书会此前读过的《红雨》,当一方试图为攻击另一方寻求一种正当时,则可能会选择将对方妖魔化为一种邪恶形象,从而提高自己行为的正义、合理性。疾病的隐喻在此时成为一种原始的自卫,以及过度的反击。
三、隐喻反应的焦虑与恐惧、迷茫
其实此部分与第二部分有许多纠缠之处,可以算是对于第二部分的总结。
疾病与隐喻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疾病被赋予隐喻的同时,也逐渐变成了某种意义的代名词。“首先,内心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伤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也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植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原文说到。探索疾病隐喻背后使用者的心理,更多的是对非我族类(非“健康王国”国民)的排斥与恐惧。本书翻译于年非典肆虐期间,而今日在新冠疫情蔓延阶段,这种恐惧仍不令人惊奇地拥有惊人的活力。
禁止武汉人进出、排斥病毒曾携带的康复者甚至是为众人逆行的医护人员被小区住户拒之门外,有家难回,长途运输司机在野地里流浪……都是焦虑与恐惧的产物。人们迷茫于解决疾病的方法,在无法解决的情境下,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隔绝,以冷漠的排斥换取自身的平安。
这不能够责怪任何人,因为大多数普通人面对未知与恐惧,能做的只是尽可能自保,同时,他们并没有对于自身文化排斥性隐喻的认识,于是按照自以为正确的方式生活。《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也有“污记论”一说,反映着人们长久以来的标签化思维,与标签的难以去除性。这也正是桑格塔战斗的原因——反对阐释。
四、反对阐释
当疾病不仅仅是疾病,而被与患者的人格、人品、生活联系起来时,隐喻就从文学艺术中的美好桥梁变成了伤人的锋刃。观察桑格塔另一篇著名批评文章《反对阐释》,可以发现,她所要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的,是那些给患者造成重压和打击的隐喻,如军事隐喻,并非所有的隐喻。就像在《反对阐释》中她表示,她反对的是某种统治性和压迫性的单一阐释,而非反对阐释本身。她拒绝的阐释,叫做“interpretation”,是解释、说明、演绎的意思,而她所希望的状态是“experience”,也即感受体验。
“经验强调面对文本时的个体感受,而阐释则是智性的人从文本中榨取结论。经验诉诸于感性,可以虚构和扬发;阐释则诉诸于逻辑,强调权威与唯一的僵硬性。经验是谦虚而包容的,阐释是决绝而傲慢的”。我们当然可以对疾病感到不适,但是一定要脱离对任何疾病都报以敌意,并将敌意延伸至患者身上的心理。
疾病不应该是被加工成的一种道德批判、心理评判或政治压迫,它应该是被接受的“无法避免”且“需要积极面对”的。“阐释”的荒谬性和压迫性正是来自于人们深以为信和引以为豪的文学想象、政治正确和文化传统,在长期累积沉淀中,这些隐喻对许多无辜患者造成了伤害,而人们却毫无意识。
对于复杂的世界与文化,面对并不了解的事物的首要应当是“反对阐释”。感受存在,而非接受解释。但文明的普遍烙印是无法简单摆脱的,桑格塔也自嘲道:“我宁可这样预言:远在癌症隐喻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反映出来的那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癌症隐喻就已经被淘汰了”。这或许永远无法摆脱,但是总需要尝试。
葛栽莱
一、作者简介
苏珊·桑塔格(.1.16—.12.28),美国作家、艺术评论家,年生于美国纽约,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等。桑塔格的写作领域广泛,在文学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年,她的历史小说《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图书奖(NationalBookAwards)。除了创作小说,她还创作了大量的评论性作品,涉及对时代以及文化的批评,包括摄影、艺术、文学等,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在文化界,桑塔格和西蒙·波伏娃、汉娜·阿伦特被并称为西方当代最重要的女知识分子。
二、主要内容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艾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三、读后感
没有人能在一生中逃过大大小小的疾病,或是一次不痛不痒的小感冒,或是如今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然而疾病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给人的身体带来伤害,更在于在精神上多方面压垮与摧残人。
在本书中桑塔格描述了结核症与癌症等这些广为人知的普遍疾病被过度解释并贴上刻板符号标签的现象。结核病带来的面色潮红是精神饱满的象征,病态的白瘦弱是高等阶层忧伤与浪漫的象征。让我想起古欧洲“蓝血贵族”身着化工颜料染制的礼服,铅粉下惨白的脸庞病态而骄傲。相比于结核病是活力消耗的疾病,癌症是绝望、无情、残忍、恐惧的代名词,梅毒是羞耻、滥交、亵渎的代言,鼠疫是社会混乱、污染、反常的瘟疫。大多数时候疾病并不再是疾病本身,它更多含沙射影地指向患病群体的阴暗面,像是患病者不是一个可怜的受害者反而像是负罪者,是该疾病相关联的所有丑恶的集中。
“标签化”在当今快餐式生活、碎片化阅读的时代更加突出。在信息爆炸的浮躁社会中,部分人难再对所见进行深入的了解与思考,试问相比于截取几个关键词,代入标签,有谁愿意花费时间摒弃成见了解真相呢?鲁迅先生曾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提起艾滋病,立刻就想起滥交,立刻就想起生活作风不正,立刻就想起卖弄风骚、水性杨花,立刻就紧蹙眉头,恨不得往地上轻啐一口。艾滋病人确诊的时候可怕吗?可怕。那时他将第一次将自我定义为病人,但更可怕的是从此他可能时刻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即使病情不被揭露,也担心旁人的有色眼光。艾滋病人的自我定义将始终如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他的头顶。可能只是因为自愿献血时一支不洁净的针管,可能只是受伤失血时使用一包混有艾滋病病人血液的血包,艾滋病的阴霾便将他们笼罩。
曾看过一场社会实验的实录:身体健康的up主戴着口罩、鸭舌帽,手举着带有“我患有艾滋病,陌生人能给我个拥抱吗”字样的牌子,背对人群,站在闹市街头。8个小时的站立,数千人的擦肩而过,五十余位好心人的拥抱是那个秋天最动人的景象。患病群体需要拥有大众的理解与关怀,而不是疾病的隐喻之下的刻板印象。
让疾病只是病,让病人只需要应对身体上的病痛,而不是延伸之后的社会压力与道德谴责。正如桑塔格所说:“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即使是如癌症式的重病,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不是上帝抛下的罪罚,不是老天降下的灾祸,不是难以启齿的丑闻,没有特定的意义,更谈不上因果论式的“正义”。
费宇
正如译者卷首语所言,《疾病的隐喻》一书的主题是关于“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在行文的过程中,桑塔格不断穿梭于结核病、癌症、麻风病、梅毒、艾滋病等疾病中间。通过文本和现实中人们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出,疾病的隐喻并不统一。
首先,疾病也是有鄙视链的。桑塔纳书籍的第一部分对结核病和癌症作过比较详细的对比,虽然同样具有不治之症的意味,但是结核病的隐喻显然好过癌症。例如,结核病往往能够超脱躯体而具有某种精神性,“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而癌症患者则没有此种自我超越性,“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
其次,疾病的隐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结核病的隐喻被浪漫化了起来。它被认为是一种高级的疾病,此病的患者也被认为是情感充沛的人,他们的心理因为患病而复杂化,他们的人格因为患病而得到了升华。在此种情况下,生病是使人有趣的方式,健康反而是无趣和平庸的。对于此类浪漫化的隐喻,我认为要将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相互分离,文本的浪漫化处理并不能抹除患者的病痛与其逐渐走向死神的事实。作者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写道:“尽管立刻浮现在我头脑里的,是文学作品中有关结核病这种有吸引力的疾病的更多的例证,我却发现了现实生活中被诊断为癌症的人,他们并不生活在(文学作品)中。”更加接近生活真相的是,疾病在各个维度被污名化对待。
从道德层面上看,患者的患病事实常被认为是一种惩罚或因果报应,而健康则证明了良好的品德和节制的生活方式。比如“染上艾滋病被大多数人认为咎由自取,而艾滋病的性病传播途径,比其他传播途径蒙受着更严厉的后果。”倘若遇到瘟疫,更会被认为是上天对于特定群体的惩罚。从社会层面上看,疾病是一种非常态化的生活状态,通过患病,患者被从健康世界中区隔开,他们成为社会中的异类而遭受排挤。也正是上述负面的疾病的隐喻,使得不幸的患者不仅要忍受病痛和死亡的压迫感,还需要忍受社会加诸于其身上的耻辱感。
诸如疾病的隐喻,处于现代社会的我们已然不算陌生。就拿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在人们还没有适应疫情所带来的种种不便时,愤怒的人们将矛头指向了野生动物的食用者们,并认为疫情是大自然对于贪婪人类的惩罚。而来自疫情严重区的人们,出于安全或其他原因的考量,在一些场合下也被区隔对待。
桑塔纳在书籍的第二部分披露了自己的写作目的,即“平息想象,而不是激发想象,不是去演绎意义,而是去从意义中剥离出一些东西。”当我们动手将现象与本质,本体与隐喻相分离时,我们还需要对隐喻本身进行更加深入的认识。
隐喻是人类思考的基本方式,它拓展了人类思维与表达空间,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名他物”。在《红楼梦》中,隐喻用以解读人物价值追求和命运归属的一把钥匙。比如林黛玉本体为绛珠仙草,绛者,红也。珠者,泪也。读罢全书,不难发现黛玉的命运基调便是“情情”,偿还神瑛侍者一世血泪。再如大观园诗社以柳絮为题填词,众人皆为伤感无奈之意,唯有薛宝钗“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其欲在这仕途经济的世界中扶摇直上之好胜心昭然若揭。上述隐喻是一种非常规化的隐喻,它只存在于特定作品之间而没有被普遍化。
因此,不是所有的隐喻都要被从本体中剥离出来,恰恰是那些常规化的、带有社会偏见的隐喻,才需要进行洗涤和复归。比如在当代社会,女性往往避免与“肥胖”这一标签相关联,这一方面体现出了当下审美的狭窄化,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了肥胖的负面性隐喻:不健康的、自控力差的、懒惰的,然而事实却并不如此,肥胖的隐喻带来了比肥胖本身更为严重的后果。
王瀚珠
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疾病不仅是客观存在的对人体造成损害的复杂过程,更成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隐喻,被附上许多社会文化、政治意味和道德评价,且这种隐喻被广泛地用于社会生活当中。虽然梅毒、麻风病等疾病也会被当做隐喻,但最常被用来当做隐喻的疾病是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与此同时,虽然心脏病同样会夺去人类的生命,但这类疾病却很少被用作隐喻,究其原因,相较于心脏病而言,结核病、癌症具有复杂的成因,且隐喻流行之时尚未得知此两种疾病的致病原理,人们对其缺乏了解,更容易为其披上神秘色彩。
十九世纪时,结核病是这一时期最为普遍的致死原因,由于对此种疾病认识不足,不仅结核病本身被赋予道德色彩,就连结核病患者也会被认为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人。随着链霉素和异烟肼的出现,人们找到了结核病的有效治疗方法,流行的疾病隐喻从结核病转变为癌症,由于癌症患者区别于结核病患者的生理表现,加诸在癌症上的隐喻也有所区别。结核病使患者出现发烧的症状,这种症状使患者被认为是患上一种因为激情太多而导致的疾病,激情的燃烧所以导致了发烧的症状。而癌症则相反,由于情感的抑制最终导致人的细胞从内部发生病变,这在生理层面则导致了肿瘤在身体内部不断扩散。结核病的“燃烧”让结核病的隐喻带有激情四射的浪漫主义色彩,癌症的“情感压抑”让癌症的隐喻带有轻蔑之意,从而联想出了癌症患者的不善表达、生活失意。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会用“与癌症作斗争”的表达方式鼓励癌症患者,将癌症视作敌人看待,将癌症视为不治之症,徒徒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由于癌细胞不断扩散、失去控制直至吞噬生命的特征,癌症的隐喻也被用作比喻社会政治的失序、经济秩序的崩溃等社会现象。艾滋病的隐喻就更为明显,即使今日人类已经对艾滋病的致病原理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传播方式所导致的世俗对于艾滋病患者的轻视和鄙夷现象仍然存在并可能在较长时间内不会消散。
随着结核病有效治疗方式被发现,结核病所带来的隐喻也逐渐消失在人类的视野中,疾病的隐喻随着疾病认知的改变也在不断地被改变着,当一种疾病被治愈,人类对这种疾病的恐惧也会逐渐消失。疾病隐喻出现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存在一种难以被揣测的具有神秘色彩的致死性疾病,疾病被治愈,隐喻也会逐渐消失。致死性的疾病总是存在的,一种疾病的治疗方法被发现,新的疾病却也不断被发现,隐喻可以被替代,但却不会消失,疾病的隐喻,总是与人类对疾病的认识密不可分。我们无法消灭这种隐喻,也就无法消灭因疾病的隐喻所导致的患者心理负担的加重情况的存在。
张霁晖
为了形容和表达方便,人们常常会用一种事物去比喻其他事物,这是不可避免的。只是尤其在疾病这一领域,将疾病抽象成一些特征,并将其用于形容其他事物,会给疾病本身以及患病者带来巨大的反噬。应该说,在给该疾病概括特征时,就已经赋予了他们一定的偏见了,然后当比喻的模式逐渐广为传播并接受时,这些偏见就随之固定并在人们心中扎根。当语言产生和人类群体不断扩大时,就应当想到终有一天语言内容的不断发展带来的语义交叉及其可能会导致的对某一事物或某一群体的特征和内涵的固定。只是,当其中一些群体由于诸多原因本身就出于弱势地位时,就会引起人们关于这种联想和比喻到底是否正确的思考和怀疑。就像此前美国从弗洛伊德事件开始的一段风波一样,当中也有不少人将矛头对准了影视作品,书本,甚至于语言用词中一些所谓可能涉及种族歧视的地方,虽然大部分都是无端指责。很久以前,也有不少人针对字词中的所谓性别歧视问题吵了很久,提出要进行改革把这些字词做修改。这些诉求到底是为权利而斗争的伟大之举,还是玻璃心没事找事?毫无疑问,在这些字词表达和用法最初产生之时,肯定是充斥着歧视与偏见的。但是,到了现在总的来说已经相当文明化和现代化的当下社会中,还要去纠结字词上在最初产生时遗留下来的形式,到底是否还有意义?且不说习惯和简便与否的问题,即使不再使用这些用法,不再用癌症或结核病去形容其他的什么东西,人们对于病人的和病人对于自己的看法依然不会改变。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心理习惯的问题。人们不会用梅毒去比喻其他的什么事物,但还是会由于部分病因的关系本能的歧视梅毒病人。作者提出正视疾病,让他们回归本身的出发点是对的,但其后续的关于疾病的名词在其他方面运用的相关说明确不能很好的说明这一点。事实上,许多疾病确实能反映出病人的心态和周边环境等问题,要普通人不以特别的心态来看待他们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是不科学的。只能说,即使认识到这些,仍然要对他们抱以尊重和不歧视的态度。而把一切都归结于这个社会的弊病是不合理的。
杨绪甲
读完《疾病的隐喻》一书,有以下几点分享:
一、从写作角度看:本书英文原著书名为IllnessasMetaphor.“Metaphor”一词就是隐喻,暗喻的意思。英文中修辞中喻法有明喻和隐喻,隐喻是用一物比一物,这两物具有相似特征,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隐喻一般不用比喻词,用此修辞为揭示背后含义,比如大脑和计算机主机,就是揭示二者都具有处理信息,统筹功能。本文作者大量使用隐喻修辞,突显文学批判态度。
二、回归到本书,我总结了多处作者所作疾病的隐喻:
1.古神话中,疾病被隐喻成上帝降罪;
2.荷马史诗《奥德赛》等古书中,疾病被隐喻成上帝惩罪,魔鬼附体,天灾和报应;
3.在近代,人们观念上:结核病被隐喻成热情过度消耗,净化灵魂;富于浪漫色彩,适宜柔弱之美;权势象征,比如很多暴发户都会说自己有结核病,以此彰显阶级;以及艺术上,隐喻为悲伤、抑郁文学。同时,癌症会被隐喻成折磨毫无激情之人,无欲情绪之人;成功者对失败者的怜悯;罪犯人格构成;以及隐喻为灾祸等;
4.在战争方面,对于癌症的隐喻富有作战色彩,比如化疗,放疗,免疫系统等词都源于作战用词;
5.在意识精神方面,结核病被隐喻为意识精神化,癌症被隐喻为意识沉压,精神中强大的敌人和远大精神目标;
6.在社会方面,作者将疾病隐喻为社会腐败不公平,对社会秩序的焦虑。比如会常说社会的弊病,社会的癌症;
7.在政治哲学方面,疾病被隐喻为国家失序,以及提出的的治国术应对于此,以强化反应达到理性反应;
8.在现代社会革命中,疾病被隐喻为政治邪恶,正如法国大革命的混乱被喻为中风,纳粹把欧洲犹太人喻为梅毒,以及中国四人帮被喻为中国毒瘤。
再究其背后原因,其实作者借此隐喻,为表达以下几点:
1.政治上,抨击当时的资本主义治理没有用在刀刃上,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患上社会癌症;
2.道德人性上,因为作者父亲身患结核去世,而作者自身也身患癌症,折磨之下感同身受,写下此书。疾病的隐喻带来痛苦来源两处,一是源于他人,人们对于疾病的未知、恐惧,以此以隐喻作为攻击他人的工具,隔绝自己和那些病人距离,与这些病人宣战,可是对于这些患病之人,身体忍受疾病折磨,精神上经受他人的折磨;二是源于病人自身的逃避,因为害怕身败名裂的标签,不敢去就医和面对人,病情加重,传染更甚,因此痛苦不断。
三、作者对于艾滋病和瘟疫的隐喻也极富有现实意义。首先,艾滋病被第一世界的政治偏执狂用来攻击打压第三世界,在对艾滋病讨论中,一定要强调来源于非洲,非洲对世界的入侵和污染,这其实是政治上疾病被用来打压第三世界的工具;其次,疾病的隐喻也是对异邦想象的污蔑,隐藏有关邪恶与非我。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比如英国口中的法国花柳病,巴黎所言日耳曼病,美国所说西班牙大流感,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令人记忆深刻,就是爆发初期,国外一直以“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中国肺炎”污名化中国,这些都体现出新的疾病会会和对异邦的想象污蔑联系在一起,排他非我的态度。
四、对我来说,这本书的启示也有很多:病人面对疾病的态度,不是回避,而应该是直面和勇敢;对于健康的人来说,我们更应该减少对于疾病的隐喻,减少对于病人道德上批判,而是转向对于疾病本身探究和对批判和穷尽;以及对于人类群体来说,疾病的正名化,实现面对疾病的命运共同体,依靠每个人走出疾病的隐喻。
刘晓倩
《疾病的隐喻》一书由桑塔格两篇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结合而成,通过对结核病、艾滋病和癌症隐喻的分析辩证批判了这种从道德到政治压迫的过程。
疾病隐喻的变化往往与社会结构的变化紧密相关。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飞速发展,与之相伴的则是资产阶级的崛起。相对地,封建旧贵族则在经济上失去了原有的地位。而年议会改革后,旧贵族在议会中的席位占比大大减少,下议院(由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构成)成为英国政治中心。为了保住旧贵族在文化上的地位,文学家们将结核病裹上优雅的外壳,使其成为一种具有文学意味的“贵族病”。而癌症由于其患病部位的尴尬性(肠、胰、乳腺等)以及发病的迅速性,成为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资产阶级病”。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西方国家,医生往往不会向癌症病人提及他们的病情,而是以一种隐晦的方式,向病人的家属传达相关意思。在人们眼里,癌症是令人厌恶的,患癌病人不仅要承受生理上的痛苦,还要时时刻刻面临他人异样的目光——从道德上的批判再到政治上的压迫。
作者试图去除那些强加在疾病上的非必要关涉,让患者在面对疾病时不再需要应付额外的困扰,在一定程度上说,现代医学的进步帮助做到了这一点。早期癌症已经可以治愈,这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消解了人们的疑虑与恐慌。然而在当代,对于患癌病人的歧视仍然存在。就这一点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康雅楠
处于现在的境况中,阅读《疾病的隐喻》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桑塔格在书中称,产生疾病的隐喻的主要原因是:发病原因不明,或暂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在过去,疾病往往和文化等级等联系在一起。首先带有阶级性寓意的便是肺结核,在资产阶级兴起伴随着贵族阶级没落的时代,在经济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之上双双失利的贵族阶级企图构建其在文化上的领导权。因此,他们便致力于追求高度的精神性文化。结核病成了高贵、优雅、精致的代表。而癌症,却被视为一种身体病。究其原因,是因为癌症被视为资产阶级堕落生活的象征,贵族们把自己所谓的“气质”依托在了结核病之上,使其成为具有贵族色彩优雅浪漫的疾病,而留给资产阶级的意向则是癌症、中风和痛风等被认为是情感缺乏的疾病。
此外,疾病经常还是道德评判的工具。其中,艾滋病是最为典型的代表,罹患艾滋病的人被认为私生活放荡,这种为患病打上耻辱烙印的做法的后果便是:“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是疾病的牺牲品。”他们不仅要承受疾病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还有带有道德审判的心理压力,这将会妨碍患者接受正确、及时有效的治疗。
此外,正如译者程巍所言:“疾病的隐喻还不满足于美学和道德的范畴,它进场进入政治和种族的范畴,成为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对手、异己分子或敌对力量的最顺手的修辞学工具。”瘟疫及疾病尤其是流行病等邪恶之物被认为来自于异邦的侵入,本质上是一种将疾病符号化以区分“本族”和“非本族”。
“疾病本身一直被当作死亡、人类的软弱和脆弱的一个隐喻”,这种修辞使得疾病获得诸多的“意义”而失去其本来的面目。然而不得不承认,医疗水平的进步为疾病的去符号化提供了巨大的动力。“我们这个时代大部分善意的公共话语表达出了一种愿望,即直言不讳地谈论哪些有可能导致全面灾难的种种不同的危险。”本书对于疾病旧有的隐喻的挑战对我们当今时代背景下面对疾病的态度仍有非常重要的启示,即去除疾病的“意义”,恢复它们作为一种生理现象本来的面目。
编辑:陈泓锦
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以下是律豆博士系列作品-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
长按下方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处:网站地址 http://www.soegm.com//kcywh/13392.html